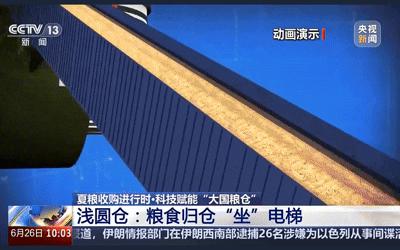对话 | 大国小农,如何走好农业现代化之路?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潮流,近代以来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人的共同夙愿。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的百年奋斗历程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更不同于西方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任务,抓住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抓住了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牛鼻子。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该如何把握和遵循党在三农领域探索出的宝贵经验?如何认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如何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本期对话孔祥智教授。
孔祥智 孔祥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合作社研究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起草小组成员。
首要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有这么几方面的经验非常重要。第一个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和完善,实际上就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党在农村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的一条基本经验,已写入宪法。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由于各地实行土地承包的起点不同,为更好稳定农民预期,1993年11月中央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施行,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进一步强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地位,从财产权角度保障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个结论被纳入2018年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更加巩固和完善了。
第二个是在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发现了规模经营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土地流转的规模化经营,一条腿是社会化服务的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这条路应该说更重要,因为即便是土地流转规模化,也是需要社会化服务的。201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全国有2.3亿户农户,其中2.1亿农业经营户,户均不到10亩耕地,土地细碎化是非常严重的。这就导致学界对于小规模经营能否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个问题存在多种看法。实际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人就有这种观点,中国的小农业怎么办?有人认为要像西方一样实行土地规模化。在长期的探索中,包括经济学界在内的学术界,一些人单纯从效率角度强调土地规模化经营,一提到农业现代化就是土地规模化,认为二者是画等号的,实际上不是这样,起码从中国来看不是这样。回头来看,走很多弯路的原因在于,认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走土地规模化的道路。近几年,土地流转速度经过前期快速增长后放慢了,而农业社会化服务却发展迅速,有力促进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第三个是关于粮食安全。之前我们一直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奋斗,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党带领全国人民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实现从温饱到全面小康的跨越。但我们发现依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比如从吃饱到吃好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何解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多国提出禁止稻麦等主要农产品出口,实际上对中国的影响不大,因为我们的口粮是绝对有保障的,但是一度引起了一些城市的恐慌,这说明国人对粮食安全的心理底线还是比较脆弱的。去年中央首次提出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强调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饭碗要一起端,责任要一起扛,必须要落到实处。同时还强调18亿亩耕地要落到实处,不能盖高楼用好地,而增的地有的增在水塘里、有的增在山坡上,增的全是荒地,那怎么行!必须把18亿亩耕地红线实实在在落到实处。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比如我们的营养结构、食品结构问题,比如农业技术创新、种子问题等。总而言之,与粮食安全有关的基本方面必须保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以服务过程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孔祥智:中央提出,要“从实际出发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有效途径”“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经过多年探索实践,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形成了“存量资产量化型”“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型”“农民投资入股型”“资源加资本型”等多种形式。
产权明晰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近年来开展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对集体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山东省东平县是我们调研中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长期以来,村集体“三资”主体不清、权责不明,致使农民主体权益缺位,出现了集体资产流失的现象,村集体经济难以持续发展壮大。针对这种现状,东平县通过农村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大体形成了合作经营型、内股外租型、产业经营型三种经营模式。在资源股权设置上,东平县探索出了A、B两类股的发展模式。A股为集体配置股,即集体“四荒”地与村内“荒片”地;B股为个人自愿股,即由成员以家庭承包地自愿有偿加入,实行“租金保底+分红”,确保农民承包权保值增值。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东平县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壮大了集体经济,进而提升了村集体话语权与办事能力。实践中发现,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效果越明显,农民得到的实惠越多。从目标导向上看,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是产权制度改革的归宿。
拓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还面临着理顺组织关系、完善分配制度、健全体制机制等一系列约束条件。我们在四川省彭州市小鱼洞镇看到,小鱼洞镇集体经济统筹发展的核心之处在于,创新建立了“镇—村—项目”三级集体经济组织,搭建了集体经济发展组织框架。但镇级联合社公司并不是以镇级集体资产为基础成立的经济组织,而是协助进行镇级集体经济发展统筹的市场主体。这就对以“公司”名义注册,但实际上承担“联合社”功能的镇级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性提出挑战。
再比如,小鱼洞镇所建立的阶梯式分红体系只是规定了镇级联合社公司、村社集体和项目公司之间的收益分配关系,而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收益如何分配、公积金和公益金按什么比例提取、村干部贡献如何体现、收益分配权能否继承等方面的问题尚缺乏详细的规定。另外,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天然的封闭性、保守性,在市场规则运用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市场定位也尚未清晰。这些问题不单单出现在小鱼洞镇,而是各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体系亟待理顺,集体成员的收益分配权亟待落实,集体资产管理与市场运作亟待提升,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需要开拓。
真正问题在于, 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 农民增收问题必须置于城乡融合框架中解决
孔祥智: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为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央不断强调推动共同富裕,旨在实现均衡而充分的高质量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之一,将收入差距缩小在一定水平上,实现发展与共享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和谐,是促进共同富裕的要义所在。农民增收问题必须置于城乡融合的框架中解决。
在城乡、区域与群体三大收入差距中,就我国现状来看,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最为严重、改善其现状的诉求最为迫切、改善的收益最为深远。尽管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张的趋势得以扭转,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依然较大。按照城乡居民收入各自内部分组来看,城乡低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更大。研究显示,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本身就与中国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有关,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最大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最为复杂,既包含了影响群体收入差距的个体因素,也包含了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等因素,还夹杂着长期以来扭曲的城乡要素配置格局等历史性因素;既有工农业本质上在分工体系中地位不同的共性,也有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的特性,而解决之道就是坚定不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业产业所占比例的下降是客观规律,为此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不能完全依赖农业生产,需要在城乡融合的框架中加以推进。农业生产具有地域性和分散性等特点,高度依赖土地,由于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重要经济特性,所以工业化之前,人类社会经济增长较为缓慢。相较于工业和服务业,农业部门的产出效率不仅仅取决于技术进步,更取决于自然环境和生产措施。因此,农业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非农就业至关重要。此外,农业具有多功能性,除了提供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这一经济功能之外,还具有社会功能、文化功能、政治功能、生态功能等诸多非经济功能,这些功能长久以来未能在农产品的市场交换中体现出价值,但是却能够为我们找到农民增收的有效路径,即发展多功能性农业为基础的乡村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如乡村旅游、乡村康养、休闲农业、社区农业等。基于此,更需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让农村对接到城市居民的消费市场,推动现代化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民。
主持人:中央一再强调,要着眼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把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请您谈谈对此的思考。
孔祥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是密不可分的。从广义来看,农业现代化包含在农村现代化之中,可以归纳为三大方面,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要实现农村现代化,首先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提升农村现代化水平,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其次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这是农村现代化的具体化和形象化;第三要强调村庄在农村现代化中的基础性地位,加快推进村庄规划;此外还要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最终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